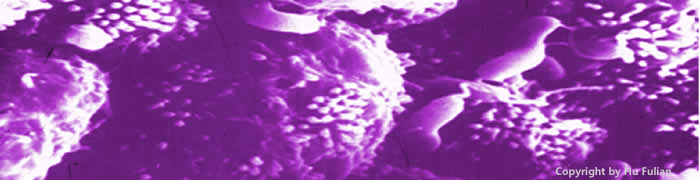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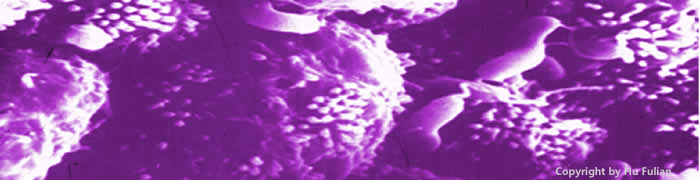
什么是幽门螺杆菌
幽门螺杆菌存在于人的胃里,是革兰氏阴性、微需氧的细菌。人的胃中是强酸的环境,还同时有消化酶的存在,这些都不利于细菌的生存。虽然有很多人曾经在胃黏膜中观察到幽门螺杆菌,但是被当作过路菌,他们一直认为没有任何细菌能够长时间在胃部强酸的环境下生存,直到1982年,澳大利亚的医生沃伦和马歇尔再次发现这种细菌,并且明确了这种细菌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关系后,这种细菌才引起医学界的重视。这两位医生也因此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奖。幽门螺杆菌是唯一能在这种环境中长期生存的细菌。
溃疡病的治疗是一个过程,需要坚持服药和复查。但门诊常有患者觉得麻烦,认为只要吃药不痛了就行了,以后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再说吧;也有些患者工作比较忙,在首次服药症状缓解后就把复诊的要求丢在一边了;也有部分患者觉得溃疡不像癌症或心脏病,不就是“胃痛”嘛,不会出现严重后果。事实上,对于及时服药按时复诊的患者来说,溃疡病是可以治愈的疾病,确实不会出现严重后果;而对那些由于不重视或没有规律治疗导致溃疡长期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小”溃疡是可能出“大”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个几年前的病例。
患者陈某,大学期间诊断出“十二指肠溃疡”,由于平时生活没有规律,常常出现腹痛。症状发作的时候口服抑酸药物就能缓解,一直没有去医院看病,溃疡病也就一直处于发作-吃药缓解-再发作-再吃药缓解的状态。他首次就诊是因为大学毕业十年同学聚会后,小陈再次出现了腹痛、黑便,按照以往的办法吃抑酸药,这次却不能缓解症状了。小陈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除了黑便还有呕血的表现,提示消化道出血的量很大。急诊胃镜显示十二指肠严重变形,这是长期溃疡反复愈合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活动期溃疡,并有活动性出血表现。由于溃疡面积太大,在经过积极的药物治疗后仍然无法控制出血,后来通过血管造影,发现在溃疡反复愈合过程中局部血管形成了血管瘤,这次出血是溃疡导致血管瘤破裂所致,药物对这种类型的出血效果很差,最终通过实施血管栓塞术才使出血停止。小陈这次因为溃疡出血住院18天,血红蛋白最低达到5.4g/dL,共输血1400mL,几经抢救才挽回生命。
像小陈这种复杂的溃疡出血虽然是少数,但是如果不规律治疗,可以使原本简单的疾病复杂化,有可能出现四大并发症:出血、穿孔、梗阻、癌变,其中出血是最常见的。对应的表现可以是贫血、黑便、呕血、持续腹痛、反复呕吐、营养不良等。所幸的是由于目前有强有力的抑酸药物和各种对症治疗的手段方法,多数溃疡并发症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得到控制,只有很少数的患者最终需要进行胃大部切除手术。而早期诊断溃疡并及时规律治疗是避免并发症最为有效的方法。
- 樊代明院士经济参考报专访报告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今年年初,国家药监局发布2020年第一号文件——《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与审评的指导原则(试行)》,在业界引起高度关注。两年前,《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在《樊代明院士:过于关注微观,医学或将走偏》报道中,樊代明力推“真实世界研究”,呼吁开展医学的反向研究。
现在,樊代明依旧忙碌,对医学发展的思考也不断深入:为何现代医学越发展,受到的质疑反而越激烈?文化之于医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重塑医学文化……不久前,樊代明再次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他郑重提出——以文化引领现代医学发展方向。
现代医学发展四大偏向
记者:您怎么看现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
樊代明: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现代医学所面临的窘境——现代医学使人类平均寿命极大提高,但是医学受到的质疑,也从未像今天这么激烈。
正如剑桥大学医学史教授罗伊·波特所写: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事实上,现代医学发展出现了四个偏向:
记者:关于O2F1,此前您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曾有过详细阐述。
樊代明:是的。这个状况至少是把简单的研究方法引入医学所造成的问题,即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引入到复杂的、可变的人体健康医疗中,医生越来越局限在狭窄的专业领域,甚至只能看某一种病,导致药越来越多,但疗效却越来越差。我重点讲后三个偏向。
现代医学成了等待医学。现代医学将人的健康状态,从没有病到因病死亡,看作一个线性的过程。什么叫病?就是根据某些指标人为地划一条线,等你越过这条线就是生病了,医生就给你治;没越过这条线,医生就不管。
以脑卒中为例。一个人没发生脑卒中时就是一个“好”人,某一天突然卒中就成了病人。脑卒中发病后,治疗几乎发挥不了太多作用,但病人一辈子挣的钱,却很可能在最后这几天给用完了。
只在疾病末期、生命最后几天发力,疗效必然有限,还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这就是等待医学。假如说我们在“病”之前多下一些功夫,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中医提倡的“治未病”,应能给现代医学足够的启示。
现代医学成了对抗医学。过去,外来、单一病因导致的传染病是人类健康最大威胁,把病都当成“敌人”来“对抗”,无可厚非。但在当今,慢性病已成人类健康最大威胁,这是人自己身体内部平衡调节出了问题,如果还采用“对抗”的思维,就是在“对抗”自己,可能治不好“病”反而伤及其他器官。
这种“对抗”思维,也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医学源自游牧文化,游牧文化生存法则是“你死我活”;而在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社会为背景的传统文化中, “和谐” “你活我也活”是主流,所以中医治癌症,是“治瘤不见瘤”,是如何更好地“带癌生存”。
医学出现了异化。把生命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身体的某些自然变化,都当成疾病进行过度干预,这种做法严重过头了。
比如,妈妈生宝宝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在怀孕过程中有点问题,偶尔去检查一下是可以的,但现在好多孕妇每一两个月都去做B超检查。要知道,每一次医学检查对人或多或少都有损伤,只是这种损伤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但有人想过吗,经常性的产检,对胎儿的远期伤害究竟有多大?多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失衡的医学文化
记者:医学发展与文化关系的失衡,或者说医学发展中文化的缺失,会给医学带来什么?
樊代明:至少有三方面的后果。
第一,在科技的帮助下,医学对人体结构乃至功能的研究已经很先进、很透彻,直达基因,但医学从文化上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还差得很远,而这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生病不只是身体得了病,更是生命得了病。医学发展与文化关系的失衡,或者说文化医学的缺失,使现代医学有些“魂不附体”。
第二,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化(包括医学文化)已形成发展了几千年(比如欧洲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但我们现在是用只有几百年的单域文化(比如医学伦理文化),去统揽甚至取代几千年的全球人类文化,从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第三,和以前相比,当代人类的疾病谱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各种内生性的老年病、慢性病,多病因多靶点;而在历史上,人类寿命从未像现在这么长,对健康的最大威胁往往是体外因素导致的、单病因的传染病。现代医学还在用简单的、线性的、直接的、在体外形成的应对传染病的方法,去处理人类现在复杂、非线性、间接的、体内自生的慢性疾病,所以常常“事与愿违”。
从魂不附体,到力不从心,再到事与愿违,这样的医学文化不改行吗?我们必须下大力气重塑医学文化。医学究竟向何方发展,取决于什么样的医学文化来引领。
记者:有人说,科技与人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偏离方向。看来,对于人类健康而言,医学与文化,也是如此。
樊代明:医学与文化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不利于患者,对医生同样会造成伤害。在追悼会上,通常会说“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却不会说“因病去世”。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严重的伤者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在通报的时候会说“因伤抢救无效死亡”,却不会说“因伤重死亡”。还有,“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抢救”,这从人道主义是对的,但在医学实践中这完全对吗?这对有些病人是劳民伤财,对医生是劳而无功,对社会是得不偿失。
“医治无效”“抢救无效”“医学追求百分之百的成功”这样已成“惯例”的话,对医生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过度的指责与伤害?这也是文化出了问题!
伤害医生的案件层出不穷,则是更为极端的现象。让伤害医生的人受到应有惩罚,甚至是判处死刑,这样问题就根本和完全解决了吗?不!一定要从医学与文化、价值观这个根源上思考,我们才有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四个坚持”重塑医学文化
记者:在您看来,处理好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应当包含哪些内容?
樊代明:
第一要坚持医学的人文性。
人文是文化在人性研究中的最高境界,其功能是保障生命的安全、生命的重要性和尊严。人性最基本要求有两个:一是追求幸福,一是追求不朽,希望长生不老。事实上生物体要不朽是不可能的。人也一样,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万事万物,无不如此,这是自然之中的必然。
但问题在于,现在单域的医学伦理文化并不承认人会寿终正寝,于是用技术去干预死亡。于是就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死亡时间从未知变为已知。二是死亡的地点从家里搬到了病房。我们过去是拿药回家养病,现在是直接把病人送到医院救死,即使知道希望不大也要尽力抢救。ICU里、抢救室里医生使劲抢救,外面家属使劲交钱。很可能最后病人走的时候,家属都没能握手告别。三是从自然死亡到了技术死亡。我院一位老专家在他92岁的时候离开了,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成了植物人,灵魂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在他身体上猛下功夫,依靠呼吸机维持。这样的人很多,虽躺在病床上却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满身插满管子却毫不自知,可以说是毫无尊严可言。医生在看管子通不通,全通就是活,不通就是不活,部分通就是部分活。这对吗?这种文化不改行吗?
过去,中西方的祭祀习俗都充分考虑了生命的神圣和尊严。时下很多医院专门开设的安宁医护,充分考虑到家属的情感和医护人员对亡者的临终关怀,事实上这也是对医学文化的一种重塑。
第二要坚持人体的整体性。
我们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生命是以整体存在的,随着无限的破分,最后所有的局部都存在,可是丢掉的是生命。反过来,所有的局部加起来并不等于一个整体,因为医学的整体一定要有生命。有生命的整体,我们才叫整体;没有生命的整体,我们叫尸体。
生命的存在,一定是依托整体存在而存在。一头大象,我们一看就知道了,盲人只能靠触摸。当盲人摸到象腿时,他能分辨出这是大象,但如果摸到细胞甚至分子,还能认出是大象么?如果再到原子、量子层面,万物已无区别,还能识别出生命形态吗?所以,医学不能太微观。
爱因斯坦早就说过,科学追求明晰性、精准性和纯粹性,是以牺牲完整性为代价的。同样,在医学上我们一味追求的“精准”,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这也是文化,是出了问题的文化。
第三要坚持生命的复杂性。
生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局部、瞬时的研究结果,不能解释生命的过程和本质,也不可能成为拯救生命的良方妙药。
我们现在认识生命,太简单了,其实它极其复杂。生命的存在,首先是有自然力作用的。否则,在没有医学的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生命是如何度过的?这种自然力,一表现为生命本身具有的抗病抗害能力;二是不同的器官能相互协调有自洽能力;三是体内的某一部分损坏后可以补偿生长,具有自我修复能力; 四是新陈代谢能力,生命体能与外界交融,吸收有序能排出无序能;五是自我平衡能力,比如水和电解质平衡、白细胞高低的平衡、热的平衡等等;六是自我保护能力,这种保护能力表现为免疫力,还表现为吃了坏东西会呕吐、排泄等;七是精神、意识对上述六种能力的反作用。
有一种说法,医生治疗疾病的“三大法宝”是用语言、药品、手术刀。其中,药品、手术刀是不得已而为之,语言的力量是最大的。西方有一句名言,“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这句话的意思是,对病人而言,舒缓和安慰是最重要的,治愈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实,即使病人治愈了,归根到底也是病人自身内在的自然力发挥了作用,医生只是在外部帮助了他们而已,绝对不要贪天功为己功。
因此,医学对生命健康的干预,应首先保证生命自然力发挥作用。如果医学的干预超过了这种能力限度,甚至取代这种能力,就叫过度医疗。从现代医学的发展实践看,医疗不足的事情越来越少,医疗过度反而越来越多。
第四要坚持研究的真实性。
现在很多医学研究是不真实的,只是一条路单向走到底,从宏观到微观,或者从结构到小结构,从长时间到短时间。一定要再走回来,重新回到宏观的层面,就是我们说的反向医学研究,只有回来的路走通了,形成一个圆圈,叫闭环式的研究,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历史上,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很多巨大成就都是反向研究而获得的。
医学研究要改变现有临床思维,要完善循证医学的不足之处,根本的方法就是反向思维。反向思维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真实世界研究。真实世界研究可能也有自身的问题,如果循证医学再加上真实世界研究,特别是在循证医学上加上反向研究,我们得到正确结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
当然,四个坚持是重塑医学文化的必要条件,只满足于这四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进来,共同为重塑医学文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向2500年前的先哲学习
记者:重塑医学文化,应当如何选择切入点?
樊代明:有人说,要解决当今诸多全球性问题,应回到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学习孔子的智慧。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有“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前看2500年,后想2500年,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树立了今人难以企及的思想丰碑。
那么,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精髓在哪里?我以为,是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整合观。整体整合医学的根源、思想脉络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在医学文化重塑上,中医整体论和西医还原论有机整合,应是不二法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万物分阴阳五行,阴阳互根,五行相生相克。在此基础上,中医提出“精气神”,精是物质,用现代医学手段可以查出,如血红蛋白、血脂等,气和神仪器查不出来,但中医大夫望闻问切可感知其状态水平。这就是结构与功能共同的表现,是古代中医对医学的认识。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依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疗效,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超出了现代医学的认知水平和疗效,值得现代医学虚心学习、借鉴。
在中医发展历史中,道家、佛家、儒家贡献良多,现代医学文化的重建,能从中获得重要的启迪。如,佛家讲修心,强调一个“净”字,要求心无杂念。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心中总是有很多杂念,能健康吗?如果天天想如何算计别人,能健康吗?又如,道家讲养生,强调一个“静”字。心态总是比较狂躁,能静下来养心养生么?所以要做到处变不惊,才能保证健康。再如,儒家讲治国、经世济民,强调一个“敬”字,要做到敬畏自然,敬畏社会,敬畏礼法。
科学本身没有目的,用好了可以造福人类,如核电技术;用得不好同样可用之杀人如核武器。用得好与不好,需要文化来引领。对于医学而言,亦是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整体论、整合观与西医的还原论加以整合,将形成新的医学文化,只有形成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其中包括整合型的医学教育体系、医学研究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学预防体系和医学管理体系等,只有这样,才能引领医学发展的新方向,才能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呵护人类健康的事业中走得更快、走得更远,关键是走得更好。
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南京巡讲-会议纪要
应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学术交流的需要,在中核海得威公司的协助与支持下,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全国巡讲南京站巡讲于2014年11月16日在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举行。来自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数百名临床医生牺牲了宝贵的休息时间参与了交流。
首先,施瑞华教授对论坛巡讲在南京举行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就上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和内镜下治疗做了专题报告。施瑞华教授用大量的图片生动的展示了早期食管癌、胃癌的内镜下表现,以及白光内镜、NBI、色素内镜在上消化道早癌诊断中的价值。卢戈氏液染色产生的烧心、胸痛等不适是临床影响碘染色广泛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施瑞华教授就如何减少碘染患者的不适介绍了自己经验,将碘容易控制在1.2-1.5%,染色后用硫代硫酸钠中和碘溶液,等可以明显减少患者的不适。施瑞华教授还结合具体病人,介绍了ESD术后出现的出血、穿孔等并发症的防治手段。其中胃ESD术后创面钛夹交替错位闭合为施瑞华教授首创,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安全性。
深圳大学核技术应用联合研究所所长马永健教授就呼气试验在医学上的应用做了专题报告。除了我们熟悉的尿素呼气试验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外,同位素呼气试验还可以准确地检测肝功能、小肠吸收功能、小肠通过时间、小肠细菌过度增殖等指标,甚至还可以检测肺癌、结肠癌。马永健教授的报告还纠正了消化科医生对尿素呼气试验的一些错误看法。14C-尿素呼气试验不仅准确性远优于13C-尿素呼气试验,并且每次14C-尿素呼气试验的放射剂量不到一次乘坐飞机所受射线的十分之一,所以14C-尿素呼气试验不存在任何安全性问题。马永健教授还介绍他们近期所做的呼气试验检测红细胞寿命、呼气试验检测维生素B12缺乏等工作。
肠道微生态是目前消化科最热点的领域,其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更为消化科医生所关注。南京市第一医院张振玉教授作了题为“幽门螺杆菌与肠道微生态”的报告。讲解了胃肠道微生态的概念、微生态与临床疾病的关系。重点介绍了微生态制剂在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中的应用,特别是微生态制剂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机理、用法及效果。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杨桂彬副教授介绍了当前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中面对的问题及应对策略。在当前严重的抗生素耐药形势下,西方国家提出的序贯疗法,伴同疗法均不适合我国国情。我国共识推荐含铋四联10-14天疗法作为首选治疗方案,可以在不预先行药敏试验的情况获得较为理想的根除率。杨桂彬教授还就抑酸的程度及患者依从性等因素对根除效果的影响做了讨论。
提问回答环节是整场巡讲的热点。众多参会医生积极提问,分别就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指征、尿素呼气实验的DOB值分析、如何选择治疗中“踩刹车”的时机、健康体检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中国幽门螺杆菌信息中心技术总监周晓炜先生介绍了面向临床医生的幽门螺杆菌专业网站的创办情况和具体操作细节,热忱欢迎大家积极参与,继续支持。
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长沙巡讲-会议纪要
2014年10月25日,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全国巡讲-长沙站开幕。巡讲由北京医学会和中国幽门螺杆菌信息中心主办,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协办,天津天士力公司承办。开幕式由北京医学会石锡军主持,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主席、中国幽门螺杆菌信息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胡伏莲教授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张桂英教授担任学术主持,湘雅医院范学工副院长做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张桂英教授做了对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现状进行了精辟分析,对幽门螺杆菌的个体化治疗进行了详细阐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吴小平教授则对肠结核和克罗恩病的诊断鉴别进行了精彩演讲,精美的图片,犀利的言辞,独到的见解深深吸引了与会专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徐灿霞教授作了幽门螺杆菌与微生态的演讲,以其内容新颖也深受欢迎。徐美华教授则做了精彩的病例分享。胡伏莲教授从医学哲学角度介绍了目前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治中的问题争鸣,介绍了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的基本概况,提出了诊治中的问题和争鸣,包括“对消化不良患者采用test and treat策略是否合适?”,“根除幽门螺杆菌是否降低胃癌发生率”,“三联疗法是否应该摒弃”,她认为这些诊治方面的争鸣实际是一个哲学问题,学术争鸣是科学发展的促进剂。在全面评估和发展的同时,还要与目前研究前沿相结合。针对幽门螺杆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胡伏莲教授对抗生素耐药作了深入探讨,提出要正确认识共识但不拘泥于共识,共识是“争议中的统一”,有时效性,需要在实践中验证和修改。提出对某些特定患者的“非抗生素疗法”的概念,并强调了中医中药和益生菌在治疗中的作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冯桂建教授则做了<<幽门螺杆菌与胃食管反流病>>的报告,报告充分回顾文献,并详尽介绍了有关进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成虹教授则报告了<<荆花胃康胶丸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多中心临床研究》,报告用详尽的数据说明了荆花胃康丸在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中的作用。中国幽门螺杆菌信息中心技术总监周晓炜先生介绍了面向临床医生的幽门螺杆菌专业网站—中国幽门螺杆菌信息中心的创办情况和具体操作细节,向大家提供了继续与专家交流的平台。巡讲大会主席胡伏莲教授及张桂英教授则对上述演讲报告进行了精彩总结和点评。
最后提问回答环节是整场巡讲的热点。众多参会医生积极提问,分别就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测方式及判断,治疗指征、尿素呼气实验的DOB值分析、幽门螺杆菌感染同时合并其他疾病的治疗时机等进行了交流。
深受欢迎、内容丰富的长沙站巡讲结束了,各位医师意犹未尽,最后中华医学会副秘长石钖军宣布第10届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十周年庆会将于2015年在北京隆重举行,北京欢迎你,北京见!
柯杨教授当选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当地时间10月20日,美国医学科学院(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the NationalAcademies,IOM)在第44届年会上公布了新一届增选院士名单,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当选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当地时间10月20日,美国医学科学院(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the NationalAcademies,IOM)在第44届年会上公布了新一届增选院士名单,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当选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Page 2 of 5